

澳门理工大学荣休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五一
上期拙作《为什么没有“志商”》,把自由的概念扯了出来——中国哲学之所谓“志”,原来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由”。
靠着《孟子》的帮助,我们把志的道理说清了,但自由没说清,考虑到自由观念与当今中国青年沉重的思想纠葛,此话题非同小可,就这么敞着口走了,感觉不合适,有负于读者,有负于青年,于是再写这篇小文,以为补充,以为注脚。
如今的思想战场上,自由是个漂亮词,也是一个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很多人都喜欢用它,如,投机谋利不叫投机谋利,叫“自由市场”,帝国主义不叫帝国主义,叫“自由世界”。特定的概念武器规定了特定的思想战术:拉自由之大旗当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
人都不愿意被人管着,当今尘世上通行的“自由”定义可能就是这么来的——自由就是没人管着。“自由世界”的舆论机器天天喊FREE这个、FREE那个,就是在这个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不受约束,个人中心,自私有理。
这个定义,与西洋哲学史上的自由概念,可谓南辕北辙。为了正本清源,我们一起到西洋哲学史上去走马观花一遭。
科学革命以前,西洋哲学被基督教统治了一千年。上帝有自由,且只有上帝有自由,人类只须跟着上帝的大自由转,故而基督教哲学并不关心人本身的自由。此前的希腊时代和后希腊时代的哲学,差不多也是一千年,主流话题是形而上学,其中也鲜有人关心人的自由问题。“自由”是哥白尼革命后被科学拱出来的一个问题。
为了理解这个“拱”字,先来说道一下科学。什么是科学?人类通过实践观察和理性分析的方法探寻宇宙实相的思想努力。注意,这说的是几百年前启蒙时代的科学,不是今天的科学。今天的科学已经不相信宇宙有实相,更不相信人类能把这实相揭示出来。而科学革命时代的西洋人确曾一度相信世界是可知的——认识一点点前进,知识一点点丰富,人类总有一天可以把宇宙的本来面目彻底看透,从而将之原原本本、一点不差地誊写到书本上。至于水落石出后的宇宙实相到底会是个什么样态,科学的原则性描述是四个字:必然王国——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客观因果的必然性来解释。
为了配合科学的此一野心,启蒙时代有好几个哲学家还构建了自己的“预见性”体系,先行用形而上学的逻辑把“这一天必将到来”的美好愿景勾勒了出来。从笛卡尔到黑格尔。

科学野心中的“必然王国”,当然包括“人”这个自然存在物。科学对宇宙构造原理的“必然性”解释,当然包括对人的生命原理和行为方式的必然性解释——人的一切行为,从内到外,都可以还原为一个必然因果体系。内,可以还原为胆汁、肾腺、血型、分泌、神经通讯等等的生化机理,人就是一个装满分子的皮囊;外,则可以还原为与猪狗无异的趋利避害的自然行为。
某甲助人为乐,某乙损人利己,那只是因为二人各自的生理心理构造不同,并不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行为,如果二人各自认为那是他们的自由选择,那只是因为他不知道事情背后的必然因果网。一切都是必然的。
一切都是必然的,自由当然就没了!自由没了,意志就没了;意志没了,选择就没了;选择没了,责任就没了;责任没了,道德就没了——人们开始感觉到科学发展所带来的这个人文悖论。
自由问题,就是这样被科学发展拱出来的。
不管科学的“终极必然性”野心能不能最终实现,仅仅是这个野心本身就已经对人类的生活构成了根本性干扰。宇宙实际上是不是彻底必然的,是一个问题;人类愿不愿意在心理上生活在此种必然之网的黑暗中,是另一个问题。世间是不是真的无善无恶,是一个问题;人类愿意不愿意生活在“无善无恶”的肮脏观念中,是另一个问题。毕竟,哲学是人的哲学,是人类为了自己活得更好、至少是活得更光明而创造出来的。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尿把自己憋死,不能用自己创造的学说给自己制造精神痛苦。必须把自由从科学手中解放出来,必须把善恶找回来,必须把道德找回来!最早发出此一呼吁的是卢梭——“人类因文明过程而丧失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原始自由。”
康德被卢梭所震撼。“我过去认为惟有知识能够造福于人类,所以我以有知识为荣,鄙视那些无知的人们。是卢梭纠正了我的偏见,教会了我尊重人。”回应卢梭的呼喊,康德以一己之力,担起了这项抢救自由的人类工程。(2024年是他的三百周年诞辰,本文的写作,或许多少有点纪念的情愫于其中。)
康德的学术目标是:实现科学与道德的和解,必然与自由的和解。实现此一学术目标的学术窍门,就是下面这一连串的“一分为二”:
1.把世界一分为二,分为可知的“现象界”与不可知的“物自体”。
物自体“不可知”,当然也就“不可思”,当然也就“不可说”,科学当然也就无法把“必然性”的触角伸进那个世界,所以,物自体是宇宙的自由基,那里没有“必然性”。科学之“彻底必然性”的思想泡沫,戳破。
现象界可知、可思、可说,科学只能跟现象界打交道,只能对现象界送来的感性素材进行理性加工——这就把科学对宇宙的彻底解释权剥夺了。你科学可以继续玩,但千万不要再说你能用必然性的因果逻辑把整个宇宙编织起来,因为你只能玩现象。
“必然”打了折扣,“自由”就有了空间。解放自由,此为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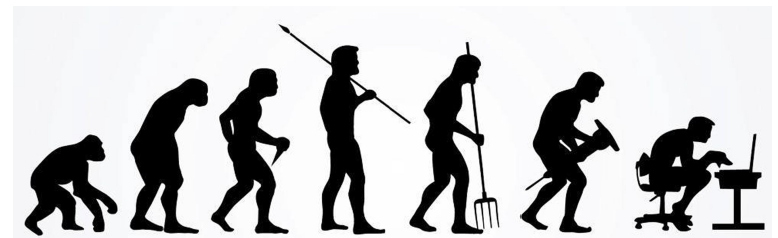
2.把理性一分为二,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
人的理性,有想事的理性,有做事的理性,两块。想事的理性叫理论理性,做事的理性叫实践理性。理论理性管认识,实践理性管意志。理论理性管“是”,实践理性管“应该”。理论理性,以实证的逻辑面对自然世界(现象界),以对知识进行“必然性”梳理;实践理性,以价值的逻辑面对人类世界,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去自由地选择人应该做的事,去创造人的道德生活。一句话,理论理性管必然,实践理性管自由。必然与自由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天地,二者实现和解。
理性不但一分为二,而且这“二”之间还有高下——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主导理论理性。道理是,若让理论理性管着实践理性,意味着因果律管着道德律,自由会被扼杀掉。反之若让实践理性管着理论理性,道德律监督着因果律,则人仍然可以在承认必然因果律的前提下找到自己自由做人的道德空间。
明显的厚此薄彼——康德对“必然”实行了“给出路”的政策,然后就把“自由”的旗帜举得高高。
3.把法则一分为二,分为“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
人的认识活动以自然为对象,遵循的当然是自然法则,但这所谓的自然法则其实并不是大自然本身的法则,(大自然没有法则,即使有,我们也不知道)而只是人的思维法则,是人对经验素材进行理论加工时所遵循的“先天认识形式”的法则,即理论理性的法则。是人的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康德谓之“人是自然的立法者”。
另一方面,“做事的理性”,人的实践活动,人的自由意志行为,也有法可依,这就是道德法则。道德法则怎么来的?也是理性立法,实践理性立法——人们在自己长期的道德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是非善恶的一套价值原则,这就是道德法则。
道德法则严格说不算“法则”,因为它并不是“必然”、“必须”的法则,而只是“应该”的法则。毋宁说它就是一个道德标杆,在它面前,个人仍有自由——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服从道德法则的自由。
理论理性为必然王国立法,实践理性为自由王国立法。自由,也有了自己的“王国”。
4.把人一分为二,分为“自然人”与“理性人”。
同一个人有两种身份:自然人与理性人。自然人,这“分子皮囊”内自有其生理构造的必然因果律;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有其逐利避害的必然因果律。总之自然人遵循的是自然法则,它是不自由的。
理性人是自由的,它的行为参照的是道德法则。注意,只是“参照”而不是“遵循”,只是“应该”而不是“必须”,否则,一遵循,一必须,自由就没了。
康德就是这样通过以上四个“一分为二”,把人从可怕的必然王国大黑暗里拯救了出来——自由回来了,道德就回来了;道德回来了,人就回来了。
欧洲思想史有一个顽固的主流观念:知识越多越自由。知识越多,人的本事就越大,上天入地,更自由了。
卢梭反潮流:知识越少越自由。大自然已经给足了人类自由,知识反而是给我们加束缚;上古原始人是最自由的,文明是反自由的。
康德一竿子打翻两船人:自由,根本就不是个关于文明状况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个关于知识多寡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个关于人之外部约束条件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个关于人的生活环境的概念;自由,是纯个人、纯主体、纯人性的,它唯一的根源就是人的理性。人人都有理性,故而人人生而自由。奴役,不会使被奴役者丧失纤毫自由,专制,也不会给专制者增添纤毫自由,因为,再说一遍,自由与人所处的境遇无关,它只是每个人的天性。
理性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增加知识,而在于它让我们的自由和道德成为可能。理性是自由的基础,自由是道德的基础——康德是为了找回道德才去找回自由的,是为了找回自由才去诉诸理性的。